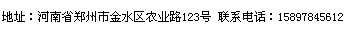安雨巷
安雨巷
那一瞬间,我突然就相信了,每个人都像被丝线牵着的木偶,在这旷广的世上重复着一幕幕的悲喜。在背后操纵着一切的就是攀附每个人心头那根深叶茂的东西,叫做命。
——题记
夕阳在天空,将大块大块的云烫出青青紫紫的瘀伤,仿佛将思绪投到上面都能感受到它们点点滴滴的伤痛,夹着伤感一点一点在空中弥漫开来。而脚下宁静的安雨巷把那金红色的阳光拉扯得很长,僵直地延伸到尽头……
这宁静的安雨巷透着一丝卑微和神秘。虽然这里的历史不过是我来时持续到现在的十几个年头,近得仿佛翻了几座小山就到了。可如同一团庞杂的根系,让我一下乱了阵脚,无从说起。却又是这个地方,让我相信了命,镌刻在每个人骨子里,不可逃脱的那种根深叶茂的定论。
01
萧俊在门口喊:“阿哲,走不走呀,你再不快点,我们就先去玩了。”
将抽陀螺的鞭子抽在墙上,“啪”的声音透过窗传进屋里。于是我急急地从床上翻出陀螺,穿上拖鞋,跑出家门,紧紧跟着萧俊身后。
桐子和萧俊是我们这群孩子中抽陀螺最厉害的,每次他们高高地扬鞭,用鞭子将空气撕裂时发出的声音,让人激动不已。他们脚下的尘土被抽到空中后久久不消散,聚集在他们的大腿以下,笼罩着,仿佛他们站在云端一般。而萧俊眼中闪烁着的那丝光芒,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么地灵动和璀璨,让人久久凝视,不愿挪开目光。
又是一个雨后的傍晚,狭窄的安雨巷如同一件未晾干的衣服,四处泛着让人避之不及的潮气,我和萧俊出门买栗子时显得有些束手束脚,我突然很想放声大闹一通,来宣泄对天气的不满,却又像被什么捆住了手脚,堵住了嘴,什么也说不出。沉闷的空气中只有路边忠诚守候的路灯冲我们眨了眨眼,然后依旧寂寞地守在那儿。
忽然萧俊让我停下,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们前方。黑暗的巷子里慢慢踱出一只黑猫,那冷蓝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我们,尾巴轻轻地撩起一片黑夜的雾气。我不由心里有些发憷。萧俊警惕地盯着猫对我幽幽地说:“黑夜中的猫都是妖怪变的,它们寻觅哪里的人更可口,然后晚上把他们吃掉。”说完摆出一个张牙舞爪的造型。我看了看他,捂住了嘴,再看看猫,它仍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时不时用舌头舔舔毛茸茸的爪子,嘴角似乎露出一丝狡黠的诡笑。地上的小水洼把天上的月光映到我脸上,显得死白死白的。萧俊不在意地拍拍我肩膀,然后冲向黑猫。黑猫矫健地跳开,飞身到墙头然后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便走回了黑暗。
“不怕啦,阿哲”,萧俊拍拍我,朝我笑了笑。
而我连最后自己怎么到家的都忘了。半夜我睡了醒,醒了睡,折腾了好几回。出了一身冷汗,不时用眼光偷偷瞄了瞄窗口,生怕那黑猫跳上窗来吃了我。夜里是死一般寂静,一丝凉意从足尖弥漫到全身每一个毛孔,脑海里满是那只黑猫诡笑着,摇着尾巴,行走于黑夜,于我的梦中,将我所谓的坚强,片片吞食……
第二天,我和桐子去找萧俊,夏季夜晚的风刮得很紧,我们不由缩了缩。萧俊的妈妈开的门,眼神有些闪躲地告诉我们,萧俊生病了,等好了再来找他吧。我从她眼里捕捉到那一丝逃避,让我有些困惑,却也没有办法。唯一值得肯定的是,萧俊昨晚一定发生了什么,莫非,是那只黑猫。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惊肉跳。于是我赶紧告诉了桐子,萧俊吓退黑猫的事。
他脸色苍白地望着我,眼中写满了恐惧。一种深深的伤感和绝望,大片大片将安雨巷的上空死死地笼罩,寂静无声……
02
又不知多久,安雨巷里我们这些孩子,纷纷到了上学的年纪。于是,每个宁静的午后,再也没有我们吵闹和大声的叫喊声,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各种乐器的交响,繁乱的声线占领着寂寞的安雨巷,显得下午无奈而又冗长。透过空气,隐隐传来两声干瘪的傻笑,如雾里的黑猫,突兀地怪叫了一声,然后掷在空气中被风吹散。没人注意是什么,正在悄然扎根生长着……
而我去找萧俊的次数随着他父母的日益苍老和不耐烦的脸而日渐减少着。犹记得开学第一堂语文课,上的是一篇神话《女娲补天》,不由让我们瞬间荡漾起的激情在随着老师淡淡的一句:“世上没什么神鬼,专心读书就好了。”而渐渐平息。我开始从心底滋生出一股浓郁的悲哀,其实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其实就算是鬼怪的存在都会让我们莫名地怀着恐惧而欣喜着。可是,我的老师一板一眼地告诉我:没有!那么就是没有吧。可我又开始庆幸。庆幸萧俊只不过是生了病,并没有离开我们。
那远方的落日并没有因满天云彩而褪色它的光芒,而是呈现出一幅更绚丽的栖霞之景,虽然后来黑暗会又慢慢地降临……
每每去问父母萧俊怎么了,他们叹息一声,那叹息声弥漫在空气中挥之不去,让我有点担忧地咬着下唇看着父母。而他们讳莫如深地没了下文。多少年后,我才明白,那叹息,不是怜悯一个孩子,而是恐惧那霸道而强大的命运,像根深叶茂的藤蔓,将人们拖入他们应有的轨道,接着生死轮回着……
一日和桐子上街买水果,路过萧俊家。正见萧俊从门里跑出来,他一面啃着玉米棒,一面又嘿嘿哈哈地傻笑着。我不禁喊:萧俊!而他依旧是笑,除了朝我把那玉米棒扔了过来,没有其他反应。而我差点被砸到,那刹那我和桐子都愣住了,见萧俊把双臂举到头顶,双手胡乱地抓着空气,两眼黯淡的没有神采,只知道咯咯地笑。
这时萧俊他妈从屋里追出来,猛地拽过他手臂往屋里拖,萧俊被拽得一个趔跌,把脏兮兮的手放进嘴里,最后朝我们嘿嘿笑了一声。然后砰的一声关门声,一切都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我和桐子从惊呆的状态醒过来。桐子皱着眉头说“萧俊好像那个,烧饼店的那个疯子。我木木地走着,张不开嘴,说不出话。我的心收得好紧,仿佛揪成一团,不知怎地,从眼里涌出液态的悲伤。
“萧俊成了一个傻子!”
“不是么,啥时候疯的呀?”
…...
大人们在萧俊一家搬回老家后,纷纷议论开来。这样那样的议论,让我忙不迭捂住了耳朵,跳进意识里的只有疯子。傻子。萧俊?我理不清,也无力从森森严严的命运里把我的凌乱的逻辑理清楚。我所能做的只是躺在床上,盯着空白的天花板。
03
十一月,冷得让人缩短了手脚,加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可还是冷。
又想起萧俊抽陀螺时好看的眉眼,霸气的神采,连桐子也不由得让他三分。而转眼,他就吊起手臂,傻笑着朝我扔玉米棒。眼里的光芒,仿佛霞光永远地消逝在夜的披襟下。再来他仿佛就永远地走出了我的生命。
有很多事我从不去想为什么。因为该来的,它就来了,该走的也会走,想要挡是挡不住的,我们也没得选择。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逆来顺受地活着。
奶奶从老家回来,告诉我萧俊得的是脑膜炎,就在那个夜晚,一只过量的链霉素打进去,于是,疯了……想起大人们小时候开过的玩笑,“小俊长得真像电视里的童星哦。”“小俊以后要了我家佳佳吧。”而现在那些大人啧着嘴,一副嫌恶又装作怜悯的嘴脸,让我打心里不舒服。
天幕降下了灰黑,将空气浸染成不透明的墨色。我躺在床上,拉紧了被子,望着窗外。我想,那只黑猫一定悄悄地走进了萧俊的梦里,吞噬了去他的灵魂,他的一切,只空空地残留着他空空地皮囊,放置在风雨中飘摇。这多残忍……
我静静地入眠,试图用睡觉来冲淡这突如其来的伤感。时光荏苒,奶奶要带已步入初中的我回趟老家,说是萧俊的姐姐萧岚要结婚了,请邻居里道儿的吃杯喜酒。因为我多年不曾回去了,奶奶于是硬要捎上我一道。听说萧岚的未婚夫是个名声不太好的,整日游手好闲的人,叫王根民。因前几辈人积了些财,加上两人挺中意对方,就结了婚。
我是个孩子,不宜发表什么议论。听过就罢了。只是那不远处,芦苇荡里萧杀的风声,单调而空寂,引得内心回荡着深深的不安。喜宴开始前,我和奶奶便先到了,遇见萧俊的奶奶,两位老人便开始寒暄起来,这时远远跑来萧俊,青鼻涕流到了嘴里也不知道,仍嘿嘿傻笑着,个子倒是窜了一大截,骨骼轮廓也清晰起来。若不是疯了,或许是个美少年呢。
可是,想象的一切都是幻影。萧俊拖着红色的破拖鞋,粗布衣上沾了大块的泥,想必在哪里打完滚回来的。突然萧奶奶在他脑勺后猛地拔他头发,疼得萧俊龇牙咧嘴地“啊”发出一声干瘪的惨叫。随后又哼哼唧唧地用手挠萧奶奶,萧奶奶一喝,吓住了他。他便老实地坐在一边。偷偷抬眼瞄了瞄我,又开始笑了起来。
我不由心里一凉,轻轻喊他:“萧俊,萧俊。”萧奶奶劝我别费劲了,他听不懂的。我有些奇怪,为什么萧奶奶要拔他头发。萧奶奶叹口气,透着无奈;“急病乱投医吧,乡里的算命先生说了,要在头上拔出一个十字,疯癫才能见好。”我看萧俊的后脑勺,根根枯草般地头发竖在肉红色突起的头皮里,看的触目惊心,隐约头皮已显出一个十字的摸样。这时他又突然跳起来,唧唧歪歪地不知喊什么,奔向刚上桌的猪脚,用手抓起两个就一颠一颠地跑到其他酒桌边凑热闹了。
在那一刻,就连我也似乎相信了,在他头上拔出一个十字的那一刻,他会变成十年前那个灵动的萧俊,那个像披着披风行走于千山万水的侠客一般的萧俊。正发愣的当儿,喜宴不觉已经开始了。萧家的女婿来敬酒。毕了,他盯着不远处,正抓食吃的萧俊,脸上抽搐了一下,显露出一股恨恨的表情。我在那一刹那,仿佛就已经看到了萧俊的未来。是什么将一切包裹在它浓茂的枝叶里,无法逃脱。我不愿,也不想,但或许这就是命吧……
04
又一个冬天来到又过去,奶奶在老家打电话过来,传来一个令人震惊却又在意料之中的事———萧俊死了。我听完,内脏似乎化成一滩血,耳畔也听不见周遭的声响,只有静静地,静静地蹲下,无助地等一阵风来,吹散这些痛,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蹲着,不知春来也哀伤。
本来王根民嫌家里养个傻子,就觉得费钱还碍事,和萧岚因这事也吵架,萧岚也做了让步,只要给他一口饭吃,能穿得暖就行了。毕竟这是她亲弟弟啊。
可不久几个附近田里的农户登门抱怨,说秋收的玉米被萧俊糟蹋了不少,本来好端端地摆在田里,被萧俊咬几口扔掉一个,糟蹋了几十根。几个农户说,他们吃些小亏也就算了,让根民看着点,别哪天出了什么大事。王根民恨得咬牙切齿:你们不说我也要处置他,看我哪天不把他扔到猪圈去!他又想起他婚礼当天萧俊毁了他心中美好的气氛。不由得火上浇油。几个农户倒是说:“根民别太过了,要出人命就不好了。”
王根民只是坐下,冷笑着慢慢点燃一根烟,然后看一片片烟雾弥漫开来……秋末,空阔的天边响起大雁的哀鸣,一声声,一声声叫得那般撕心裂肺。又一个午后,天飘飘扬扬飞起雪花,王根民趁萧岚不在家,用一只油腻的猪脚把萧俊诱惑到跟前,然后把他手脚绑了起来,先是狠揍一顿。再就仍进又冷又脏的猪圈。
萧俊叫得像杀猪一般,王根民看着猪圈里笨拙挣扎的萧俊,解气地笑了:“小子,这里的猪脚够你吃的了吧。”他抚了抚被萧俊挣扎时划伤的手臂,得意地进了屋。萧岚回家后,吵着要他放了萧俊。王根民一句话没说,用一把锁,把吵闹的萧岚给关在房间里。任凭她拼命地哭喊敲门,王根民坐在沙发上,像是在欣赏一场好戏。
屋外北风刮得很紧,密集的雪花开始飞舞着,像是来自地狱的鬼魅,欢庆着这黑暗和冰冷。呼号的风声夹杂着萧俊逐渐萎靡的干嚎。附近的人家叹息不已,“作孽啊,真是……”由于害怕王根民的脾气,没有一家人打开门去解救萧俊。
第二天,他们见到的只有风雪掩盖着的萧俊僵硬蜷缩的身躯。那干瘦的身躯,再也没醒来,他脸上划过一丝丝白缎似的光,那是最后一丝生命的流逝。
05
我不由得湿了眼眶,我努力每天去想安雨巷,将它的一切陈列在夕阳下,也去想萧俊,他杜撰的故事。至少我这么认为,是他吓唬我。可那只黑猫却变成妖怪真正走进了他的生命然后撕裂了他,吞噬了他,咬碎了他。还有武侠一般的他,吓跑黑猫的他,抽陀螺的他,编故事的他,然后,他疯了,走了,死了。
他在白光炽烈的盛夏疯了,在寒风凛冽的腊月死了。
很多时候,我就在想,已然疯掉的他在田野中蹦跳着,发出哼唧的声音时,他还是快乐的吧。但,或许我错了,他快乐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局外人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是否快乐。他有的只是瘫痪思维。像一团废铁储存在体内。我也曾想过,一个没有思维的人,他至少也应该没有忧愁,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欲望,欲望早就被那支链霉素浇熄了。
从此以后,他可以比我们少多少忧愁和悲伤?他可以不像我们被推在岁月的边缘,去猜测世上的人的心灵。可要是他没得脑膜炎该多好。或者即使得了脑膜炎,那支链霉素没注射该多好。再或者,即使注射了,他们家不招女婿该多好。最后的或者,他们家招的女婿,那个男人不心狠手辣又要面子多好。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或者,也没有那么多的多好。病了就是病了,疯了就是疯了,死了就是死了,这条僵硬的轨迹,谁也无力扭曲。就在那时我内心被一种空前宁静的东西占据了,那不是恐惧,是比恐惧更厉害的东西,它控制着每个人,仿佛木偶表演时,在幕后拉着竹竿挑线的操纵者。它紧紧牵着我们,谁也不会改变这种状态。
就在那时,我相信了命。那种甚于恐惧的情感,我终于明白了,那就是面对既定而又强悍的命运时,那种深深的,深深的无奈。这种深深的深深的无奈….安雨巷最后一户人家搬走时,板车独轮沉重滚过的声音里,房顶上,瓦愣草朝满载家具的小车招了招手。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吴文英的几句词:雨外蛰声早,细细就霜丝多少?说与萧娘未知道,向长安,对秋灯,几人老?
我微微笑了,一片寂静中,黄昏的光芒,晃悠悠地投射过来,拥裹了这屹立于斜阳中的安雨巷。这最后一个黄昏,神圣又宁静,穿过曾经曲折漫长的安雨巷,投向了远方……
文:林白
排版:今然曦
图:网络侵删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