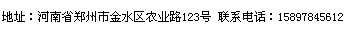我吃太多,我有病丨人间
“根本就是你贪吃,还给自己找借口!”
“吃这么多,吸毒的都没你这么变态!”
“吃东西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会失控到这个地步?”
配图
《空气人偶》剧照
换上工作服后,我推开休息区厚重的弹簧门,准备去病房交班。
刚推开门,就见过道处站着两个人——手里拿着入科病历的邓医生,和一位穿着蓝色隔离衣的中年妇女,两人都没戴口罩。看样子,邓医生是在给病人家属做入科宣教。
我走近时,邓医生的话零零散散地飘了过来:
“……还好你发现得早……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就是缺乏关爱,得关心她的心理健康……何况是你女儿这种抑郁症患者……
“……再割深点儿手腕的血管都断了,幸好她下手不重,目前也就是失血较多,肌腱伤了一点,其他生命体征还算稳定……输完血之后观察几个小时,没问题就可以转普通病房……
“病历的这里、这里……还有这些地方都需要签字,一共9处,别签漏了。”
中年妇女从头到尾只是沉默地听着,失神地看向旁边的四人间病房,嘴唇发颤。邓医生将一支黑色签字笔递给她,她接过,开始迟钝地在纸上签着字。还没签几页,她突然停了笔,撑着墙失声痛哭起来。
我悄悄走进旁边的四人间,问正准备跟我交班的同事:“外边那是哪个床的家属?”
“25床那个小姑娘的妈妈,”同事轻声回答,“割腕的。”
我无声叹了口气,看向25床的床头卡:吴茜,18岁,住院号xxxx。又看了眼躺在床上的姑娘,面容清秀,双眼紧闭,苍白的面孔毫无血色,几乎跟床单融为了一色。她左手手腕包扎着厚厚的纱布,上方悬挂着血袋和外层的加温装置,鲜红的血液正从透明管缓缓注入她的体内。
“交班吧。”我转头对同事说。
“25床刚送来,先交(接)她吧,”同事给我递过来一副薄膜手套,“她睡着了,我们动作尽量轻点儿。她是一楼急诊刚转上来的,神智清醒,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约0.25cm,心率较高,管道就一个吸氧管、两个静脉通道,静脉通道一个输液一个输血。现在翻个身看一下皮肤情况吧。”
“骶尾部背部皮肤都是完好的,”同事轻轻翻起吴茜的身体,一手扶肩,一手稳住她的髂骨处,示意我查看后面的皮肤,“但除了手腕的伤口,她左手臂内侧还有一些刀疤,右手背上还有几处暗红色的陈旧疤痕,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都写在护理记录单上了,你可以看一下。”
我“嗯”了一声,抬起吴茜的左手,仔细端详——她手臂内侧的确交错着五六道深浅不一的刀伤,其中两道显然是下了狠手,刀口翻出血肉,还未愈合。
再看向她右手手背时,我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突然有些脱力——她右手手背的指关节处,有好几块暗红色疤痕,在白皙的皮肤上十分扎眼。同事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却清楚——因为我的右手背也有一小块这样的伤疤。很浅,但一直存在。
那是反复催吐时手指与牙齿摩擦导致手背皮肤长期受压迫和摩擦形成的老茧,是暴食症曾给我打下的烙印。
暴食症,一种长期不自控地大量进食、外加后续清除行为的精神障碍症,社会普及度极低,除了患者本身,几乎没多少人知道和了解这个病症。
第二天一早,吴茜转出了ICU。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和她真正相识,且一直保持联系。在之后的交往中,或许是同病相怜,吴茜渐渐对我敞开心扉。她告诉我,之所以想自杀,是源于折磨自己多年的暴食症。
吴茜向我描述她对暴食症的最直白感受时,只用了9个字:“恶心,难以启齿,像吸毒。”“我跟暴食症斗争了3、4年,却始终摆脱不了它,太痛苦了,我只能选择自杀作为结束。”
可吴茜也坦言,最初的时候,暴饮暴食又的确给她带来了无法言喻的安全感。
12岁那年,吴茜的父亲有了婚外情。面对丈夫的背叛,吴茜的母亲在长达数月的争吵打骂和歇斯底里后,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满心愤恨地带着女儿搬了家。
大概是从搬家那天起,母亲对家庭的温情似乎就已悉数耗尽,让吴茜开始觉得陌生起来。吴茜自己也变得少言寡语,回了家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鲜与母亲交流。
在这种压抑的家庭氛围里,吴茜的母亲变得愈发焦躁,每当看到吴茜一脸阴郁时,总会不由分说,上去就朝吴茜甩巴掌,边打边问:“你丧着脸给谁看?我是对不起你还是怎么着?还要继续丧着脸吗?”
即便吴茜哭着讨饶,她母亲仍会绷着脸破口大骂:“老娘一个人在外面累死累活挣钱供你上学,你倒好,天天哭丧着脸给我看!你跟你那挨千刀的爹一样,都是讨债鬼!只知道折磨我!”
这样的打骂会一直持续,直到吴茜抹干净眼泪,扯出一张笑脸为止。
“你心情不好也不要让我看见,不然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她母亲在事后总会这样说。
于是,吴茜被强行开心,除了笑,她不敢在母亲面前显露出一丝别的表情。
这种长久以来的情绪压制,让吴茜很快在食物上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在一次次被母亲打骂后,吴茜开始躲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将所有能吃的都塞进胃里。每次暴饮暴食后,吴茜都觉得自己的肚子鼓胀得几乎要爆掉,可又感觉,那些被她狼吞虎咽吃进胃里的食物,竟像是一管速效麻醉剂一般,暂时性关闭了她身体里的痛觉。
青春期的吴茜开始对食物产生异常的迷恋。她愈发频繁地躲起来进食,食量也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她每次必须吃得胃部鼓胀得看不到脚,轻轻摸一下肚皮都疼,大脑才勉强发出停止的指令。
吴茜说,最多的一次,她起码吃了正常人5顿的食量。她知道这样不正常,自己也很难受,“可我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怎么都停止不了”。
或许在旁人看来,吴茜的这些说辞,不过是她给自己懒馋作祟找的借口,所谓的“暴食症”,更是强加给自己的“矫情病”,纯属无病呻吟。
可我却完全能明白吴茜的痛楚,因为从16岁到22岁,我也被暴食症足足裹挟了6年。与暴食症的战斗,曾让我一度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高三住校那年,我母亲因急性脑膜炎晕倒入院。医院时,母亲又突然癫痫发作,全身大幅度抽搐,嘴里不停地吐着沫子。几名医护人员立在病床两侧,死死摁住母亲的手腕脚踝,混乱中,有医生急声叫喊:“拿毛巾拿毛巾!别让她咬破舌头!”
母亲紧咬的牙关被大力掰开,呜咽声很快被毛巾捂碎。父亲则在一旁慌乱地攥紧母亲发抖的手,双眼通红。
铺天盖地的恐惧袭击了我。我站在病房门口,哭得浑身颤抖。
由于病情危重,母亲很快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全身插满各种医疗管。医生将一纸病危通知单递到我们面前时,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忘了那张病危通知单上是否有父亲的泪渍,忘了医生在耳边絮絮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天中午我吃了很多饭。
当第一口食物从口腔滑进胃里时,我悬空许久的心竟跟食物一起,落到了实地。时至今日我都记得那种痛快,记得那种全身毛孔舒张的酣畅淋漓。
我想也就是在那时,我的暴食症跟着学医的想法一起抬了头。
在母亲患病的几个月里,我将压力倾泻于食物,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我的体重就完成了从80斤到斤的飞跃,从黛玉妹妹茁壮成长为了刘欢老师。
每次暴食后,我总是一遍遍地告诫自己必须要停下来。可当食欲汹涌而来时,我便失去了所有的思考能力。大量的食物被我机械地塞进嘴里——我几乎尝不到它们的味道,只是不停地往嘴里塞,直到肋骨撑得生疼、呼吸变得困难,才会停止进食。暴食后,站不了、躺不下、坐不住,我只能侧着身体半靠在椅子上,将腿伸直,小心翼翼地缓慢呼吸。
当我意识到自己对食物的渴求已趋病态时,暴食症已死死盘踞在了我的身体里。我开始产生难以排解的罪恶感,为了消除它,我开始出现暴食症的“清除行为”之一:催吐。
一开始的几次催吐,我进行得并不顺利,往往在厕所折腾半小时,也只能吐出少量的酸臭残渣。吐完后,我撑着手往镜子里看——自己双眼通红,满脸是泪,鼻涕泡挂在鼻尖,狼狈又滑稽。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
两三个月后,我的“清除行为”换成了导泻。我偷偷从学校门口的药店买来大量的酚酞片(泻药),从一开始的1片吃到10片、更多,从“大弦嘈嘈如急雨”吃到“小弦切切如私语”,我才会停止一次清除行为。
当年虽然仅催吐了3个月,我的手上还是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疤痕。在疤痕还很新鲜明显的时候,我会下意识避免把手暴露在别人面前,害怕别人通过这个特殊疤痕发现我的怪癖。偶尔有人问起,我也只能慌乱地推说这是烫伤。
而从吴茜入科当天手上的伤疤来看,显然,她的催吐史比我久得多。
在患上暴食症的第5个月,吴茜曾在网上发了个求助帖,标题是“暴食过后很难受怎么办?”不出一分钟,有个网名为“琉璃月”的人在帖子下面回复道:催吐就行,很简单的。
在向那位网友询问了详细技巧后,吴茜就此踏入催吐的泥淖。
每次暴食完后,吴茜都会躲进厕所将手指伸进喉咙里拼命地抠,若吐不出来,便用网友教给她的办法,大量灌水后再试。渐渐地,吴茜开始享受那种快感。在她看来,母亲的无理苛责、学业的力不从心,都能简单消弭在这一吃一吐里。那些在食欲中被暂时分解的痛苦,又随着食糜和胃液一起被清出体内。每一轮暴食催吐,都能带给她一次真实可感的慰藉。
吴茜跟那个为她“指点迷津”的姑娘互加了好友,开始建立起信任和友谊。
互相熟知后,吴茜才知,“琉璃月”的本名叫李琳琳,这个看似经验丰富的姑娘,其实比吴茜还小上一岁。
李琳琳告诉吴茜,自己之所以教她催吐,是因为觉得大家同病相怜,所以她很理解吴茜的痛苦。
李琳琳得暴食症,起因是减肥。
上初三的时候,李琳琳的体重达到了多斤,比同龄女生胖了不少。班里的同学常常嘲笑她,给她起了多个以“猪”开头的外号。在枯燥繁重的学习之余,李琳琳成了同学们实施恶作剧的最佳人选:他们常常将李琳琳关在教室门外不让她进来,还在她的后背悄悄贴上“我是猪婆”的字条,甚至每当李琳琳从他们身旁边路过时,他们就会夸张地捂着鼻子,然后大喊一句:“离我远点,你身上一股猪骚味儿!”然后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这种青春期里直白坦荡的恶意,让李琳琳每一天都过得十分煎熬。她也曾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去讨好所有人,想让大家友善地接纳她,可事实证明,这只是徒劳。
躲在被窝里哭过多次后,李琳琳开始尝试各种风靡网络的速效减肥法,交替着进行节食和绝食,每餐严格计算摄入热量,就算饿到头晕眼花,都不敢多吃一口。最终,她成功地在两个月内减下25斤。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已经饿得快疯掉。
一天,李琳琳独自在家时,被野蛮压制已久的食欲突然爆发,将她倾覆。“那天我像发疯了一样,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全塞进了胃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叫嚣:吃!吃!吃!”
短暂暴食后,李琳琳觉得畅快满足,可满足之后,暴食的罪恶感又将她笼罩。为了“赎罪”,李琳琳开始用更加苛刻的节食来惩罚自己。
后来,李琳琳无师自通,学会了催吐。而在催吐一年后,李琳琳开始觉得不对劲——由于催吐时胃酸会倒流,她的牙齿被腐蚀得严重,有几颗牙甚至已快要掉落。而后续的腮腺肿大、继发性闭经也让她无比痛苦。更让李琳琳害怕的是,她曾在网上查过:长期催吐可能会导致食道癌。
于是,在网络上跟其他催吐者的交流学习中,李琳琳很快成为了更“高阶”的“管党”(用管子催吐的人)一员。
关于用管子催吐的部分,李琳琳不愿跟吴茜详说,只发给吴茜一个淘宝上购买催吐管的链接。后来我也曾点开那个链接看过,商品首页上写着“兔管(谐音‘吐’)、兔子党”等暗示性词语,销量不低。而评论和问答里,竟有不少十几岁的买家。我盯着图片上足有两三指粗细、50多厘米长的白色塑料管,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居然会有人把玩意儿插进胃里?
我点开卖家的对话框,问催吐管的具体用法。卖家告诉我:“用开水把管子泡软,或是给管子抹上食用油,然后把管子从喉咙里伸进去,一直用力吞就行了。等管子插到胃里之后,就往胃里打气,胃里吃的东西就自然从管子里流出来了。”
见我没回复,卖家以为我有所顾虑,又添了句:“你别担心,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虹吸原理,知道吧?”
还他娘的挺有学问。我叹了口气,忍不住问卖家:“你们卖这种东西是不是不太好?”
卖家用一句“关你屁事”简单粗暴地结束了对话,没再回复。前段时间我又去看了下,那家店的销量竟又涨了不少。
在这种灰色商家的助力下,李琳琳用催吐管仅半年,就多次因各医院。
李琳琳的身体每况愈下,而吴茜的情况却比她还要糟糕。在长期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吴茜不仅身体上患了病,还得了中度抑郁。
食欲不可遏制,绝望也如影随形。吴茜说,对于自己这种见不得光的怪癖,她总是会感到恐惧。她害怕自己那张惨白浮肿的脸,害怕人多的场合,更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疯狂进食的丑态。
在一次强迫性催吐了4次、甚至连红血丝都吐出来时,吴茜对自己憎恨得发抖,她拿起了刀片,在手臂内侧用力地划下了第一道伤口。
后来,当李琳琳得知吴茜自杀的消息时,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