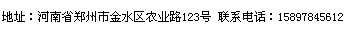粥米汤和红烧鱼
即使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四十年,母亲在和童书聊天的时候还会提到了那件事。她说:“要不是你父亲舍不得,你早就不知道去往何处了。”
何处呢?黑龙江?甘肃?或者,更远的边陲地带。
母亲的讲述波澜不惊:本来中间人已经谈妥了,要领养你的那对夫妻是部队的高干,马上转业到地方去做官儿了。他们结婚多年没有孩子,看了你的小照片特别喜欢。他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做了他们的女儿后必须和我们断掉所有的联系。我倒不难过。你做了官家的姑娘,一辈子不愁吃穿。挺好的。可你父亲不同意。他说,如果断了联系,不是连三姑娘的面儿也见不上了吗?
换成另外一个人,也许会有这样的忿然:你们有四个孩子,为什么被抱养出去的是我?
童书向来不是个拎不清的人。况且,她在外生活的十年里养父养母视她如己出,她是幸福的。童书奇怪的是,父亲那么严肃的样子,原来也有过“舍不得”的时刻。
在十四岁的童书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眉头紧锁的。言语严肃,表情严肃,对孩子们严肃,对母亲更是严肃。而母亲似乎也习惯了这样一个严肃的男人。要是她去和父亲说点什么事,父亲十回有七回是不耐烦的。剩下的三回,是根本不屑于搭理她。她碰了壁,微黄的脸膛上隐约闪过一丝尴尬。仅仅是一丝。很快的,又神色如常了。
父亲不在家,她坐在靠墙的竹椅子,一边织毛衣,一边轻快地哼唱着“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竹椅子还是父亲早前从外省买回来的,上了岁数。在母亲的歌声中一下连着一下地“吱呀”着,像个不甘心的人在嘟嘟喃喃。
这支老歌母亲哼唱过无数遍了。她年轻时是公社宣传队的骨干。宣传队去四里八乡表演,专程来看母亲唱歌跳舞的后生挤成了长队。母亲几乎包揽了演出中所有的主角,出尽了风头。她二十岁,圆脸,笑起来嘴角跳动着两只俏皮的小酒窝。红头绳绑着两条乌溜溜的长辫子,走起路来,辫梢在柔软的后腰上灵蛇般地窜动。那样一个落在很多后生梦中的、白月光一样的母亲,却在外公的安排下,嫁给了十七岁的父亲。
父亲的皮肤很黑,黑得简直能反光。父亲个子矮小,比母亲还矮半个头。父亲成天背着鱼篓在湖荡里转悠,一副吊儿郎当的做派。总之,父亲处处是配不上母亲的。但母亲最终还是含着泪穿上了嫁衣。
父亲的奶奶和母亲的爷爷是亲姐弟。老一辈的人主张亲上加亲。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父亲家太穷了。三间歪歪斜斜的草房子,下雨天,雨水就从黄泥墙上裂开的大口子钻进屋里。娶别人家的姑娘,几块钱的彩礼钱他首先出不起。小脚的老姑奶奶捏着手绢坐在娘家哥哥的遗像前哭哭啼啼地商讨了小半天,神奇地定下了两个年轻人的一生。
母亲回忆父亲第一次提着礼物登门的场景:中秋节的当天,父亲剃着“马桶盖头”,打着赤脚出现在外公家的院子里。还没来得及张开讲话,先声势浩大地擤出了两条黄绿色的鼻涕泡。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母亲下嫁了。但父亲不以为然。他长身而立,咄咄逼人地盯着母亲,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你还不是托了我奶奶的福?
这句话,被正当壮年的父亲说得堂而皇之。从遥远的内蒙古当了九年兵转业回来后被分配到县供销社运输队开人人羡慕的蓝色“大解放”。他离开家乡的九年,母亲一个人在乡下起早贪黑地耕种着好几亩的地,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养孩子。父亲的九年是一段脱胎换骨的好时光。部队里的大锅饭把曾经干瘪的他滋养得浓眉大眼,个头直窜到了一米八。母亲的九年是血色全无的。九年里,她陆陆续续地生下了三女一男。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孩子的生日落在八月里。八月,是父亲两年一度的探亲假。
童书的大姐童琴不止一次地当着丈夫的面数落母亲,说父亲回家探亲的日子里,母亲晚上总是狠心地把她一个人丢在耳房的大床上,还不许怕黑的她哭出声来。
比童书大十岁的童琴不记得自己八岁那年得过的一场病毒性脑膜炎。医院待过的大半年。不记得母亲搂着她睡在病床上的每一个夜晚。母亲白天手脚并用地忙完了所有的农活家务,还要风雨无阻地在夜幕下医院陪她。她记得最牢靠的是母亲对父亲的顺从。刻薄一点说,是巴结。
一开始,母亲打算把老二童棋送出去做养女的,可七岁的童棋年龄偏大了,人家生怕养不熟。于是,母亲临时替换了三岁的童书。童书的后面,还有个小一岁的弟弟童画。
开了几年“大解放”的父亲有一天回乡下的家中向母亲提出了离婚。他的理由是感情不合。母亲哆哆嗦嗦了半天,壮起胆子问父亲:感情不合,你还和我生这么多孩子?
父亲觉得母亲不可理喻:老童家的香火不能断在我手上吧。
父亲采取了迂回的战术,他跑到了童书外公的门上,要老丈人出来主持“公道”。童书的外公在他们队里做了三十多年的队长。老队长是讲究策略的,当然不会和意气风发的女婿撕破脸。他客客气气地和女婿说:你坚持要离婚,我不反对。离婚是因为我女儿犯了错吗?
“不是。”童书的父亲老老实实地回答:“你女儿很好。”
出了轨还不觉理亏的男人都一样-----我知道你很好,但我就是不愿和你过。
离婚的事明里暗里地闹腾了几年,母亲的地位保住了。那个企图撬走父亲的姑娘熬不住乡间的风言风语和长长的等待,悻悻然地嫁了人。
母亲的胜利是表面化的。外人面前,她夫贵妻荣苦尽甘来跳出了农村,住进了父亲单位的宿舍楼,有了个亮晃晃的城里人身份。在父亲那儿,她所谓的胜利之上,覆盖着的是绵绵不断的失败。
母亲作为转业军人的家属,上级本来是安排了一份工作给她的。父亲讲话的分量远远胜过上级。他问母亲:你去上班了,孩子谁管?家里的事情谁来做?
父亲管的是赚钱养家的大事。牛气得很,动不动叉着腰吼一句:你们靠我吃靠我住,离开了我,看你们怎么活!
母亲谦恭地低着头,不置一词。孩子们更是不敢吭声。纵然是这样,母亲还要帮父亲辩解,她说:你父亲真的没有坏心,就是脾气差了点。我不计较他。
童书吃不准,母亲的这句话究竟是在宽慰孩子,还是她的自我安慰。
家里大大小小的杂事归母亲管。母亲天不亮就起床了。宿舍楼狭小逼仄,她坐在门边上轻手轻脚地搓洗着衣服:咔嚓,咔嚓。。。父亲躺在床上咬着牙抱怨:“起那么早干什么?烦死人了!”
幸好,父亲一个月中有过半的时间在出差。他嫌烦的次数和母亲的“被嫌烦”才不至于交叠得那么稠密。
洗完了衣服的母亲走到阳台一角的煤炉边炖粥米汤。父亲爱喝粥米汤。他在家,母亲早晚都要炖。每逢他出差,母亲就去楼下的传达室里翻看他的出行记录,掐着他返程的时间准备粥米汤。很少的一点米,放一锅的水。在煤饼炉上笃笃地炖上半天,炖得米融化在汤里,汤变成了乳白色。如果是端午节前后,母亲还会去菜市场买来包粽子的新鲜青箬放在锅里一起煮。这样的话,粥米汤就是好看的翡翠色。盛夏的下午,阳台上热浪逼人。母亲炖好了一锅米粥,上衣全被汗水渗得透透的。
父亲进了家门,洗去一身的风尘。桌上早有一碗温热的粥米汤等着他了。他的头发还是湿润的,大刀金马地往椅子上一坐,搬起碗,很响地吸溜了一大口粥米汤。然后,心满意足地吐出一口长气。童书能看到谄媚稳稳地占据在母亲脸上的每一根法令纹里,她目不转晴地盯着父亲的碗,以便随时随地伸手为他添粥。她的眼里、心里装着的都是父亲。做饭做菜全照顾了父亲的口味。父亲爱吃炒螺蛳,她不厌其烦地剪螺蛳屁股。螺蛳屁股硬得很,她右手的大拇指上剪出了好大的血泡。父亲爱吃大蒜,碗橱里长期备着一瓶她亲手腌制的蒜酱。父亲不爱吃面条,只有他出差了,母亲才系上围裙给馋着面条的孩子们做几回手擀面。
母亲的乳名叫德芳,童书一次也没听父亲喊过。父亲喊母亲,“嗳”就是开场白。“嗳,你来干什么什么。”“嗳,你去干什么什么。”
轻飘飘的“嗳”来,又轻飘飘的“嗳”去。
那个女人来家里的一天正好是周末,一家人都在。父亲推门进来,女人大大方方地跟在父亲身后。女人的皮肤白白的,烫着时髦的卷发。童琴冷哼了一声,昂首而出。父亲手上拎着几袋子熟食朝着碗橱的方向瞄了几眼,扬声叫母亲:嗳,你拿几只盘子出来吧。
桌子是母亲拉开的,熟食是母亲盛好的,碗筷也是母亲分发的。开饭了,她还在阳台上炒菜。锅铲叮叮当当地敲着锅底。父亲吃了一半,想起了什么似的,对着窗户喊了一句:嗳,你还在忙什么?
那个陌生的女人也软绵绵地开腔了:“大姐,你一起来吃饭吧。”
“你们吃吧,我不饿。”母亲的回应低低的。窗纱上蒙着的一层薄薄的灰尘,童书看不清母亲脸上的表情。但母亲当时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有着十分的心虚。
女人吃过饭后走了。父亲开着大解放往修理厂去了。过了一会儿,母亲也一反常态地出了门。一直到天很黑很黑了,才默默地回到家中。除了眼皮子有点肿,其余的,倒还正常。
她走进里间帮睡在上铺的童画掖了掖被子。下铺是童书童棋的地盘。童书眯着眼假装熟睡。母亲没有惊动她,猫着腰去问躺在另一头的的童棋:“你们三个人晚饭都吃饱了吗?”
三十多岁的童书有一次莫名其妙地想到了那个她装睡的夜晚。她问母亲,天那么黑,你一个人待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母亲说,我能干什么呢?就在护城河边上来来去去地瞎转悠着呗。童书说,你没打算往护城河里跳?母亲苦笑着看看童书:那个女人和你父亲几十年没断,她自己也有个儿子,不可能为你父亲离婚的。万一我跳下了河,谁来给你们洗衣做饭?
童书撇撇嘴:你多伟大,活着好像光是为我们做饭似的!
父亲的几个老同事来家里聚餐,母亲烧了一条红烧鱼,客人们吃了全赞不绝口。父亲笑了笑,难得地夸了母亲一句:老卢这个人,别的没用,红烧鱼倒是做得顶呱呱的。
从天而降的一个“老卢”取代了“嗳”。母亲像忽然间熬到一个新的身份一样,惊喜不已。她依靠着这声转折性的“老卢”维持着后半生中那些阴晴不定的日子,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红烧鱼的各种做法之中。只要父亲领着朋友来家里吃饭,她都要做一道红烧鱼。锅是煤气灶上的小铁锅,鱼是大个头的青鱼。小的锅,大的鱼。她偏偏有足够的功力和耐心烧出又鲜又美的鱼。出了锅的鱼头尾完整,身上的皮一点也没有擦破,色香俱全。她挺着粗壮的身板儿立在桌边,眼睛亮晶晶的。看得出,她是多么地希望得到父亲的表扬。父亲却专注地和客人聊着天,吝啬得连一个“好”也不给她。
母亲的婚姻生活中,炖了无数锅的粥米汤,烧了无数条红烧鱼。父亲退休了,母亲不再为他炖粥米汤。父亲的血糖超出正常值两倍多,吃药也收效甚微。医生说,高血糖的人喝粥米汤是雪上加霜。父亲得吃干饭,最多两调羹。家里已很少来客人了。来了客,母亲也懒得烧红烧鱼了。她急着赶邻居的麻将之约,哪里还有当年在灶台边一站几个小时的耐心。她在小区的楼下大声地喊着父亲的名字:童大强!童大强!你下来帮我提一下菜篮子。
童书听着她的高分贝,暗自发笑。她问母亲:“你这么咋咋唬唬的,就不怕父亲翻脸?”
母亲得意地摆摆手:他现在泛不起什么花头经了,我可不怕他!她说得活像真的全身挂着胆,全然忘记了前不久的一次落荒而逃。她和父亲发生了口角,一怒之下,居然往父亲的腹部捣了一拳头。突兀的一击使父亲膛目结舌,不敢相信。母亲愣了一下后火速撤出了战场。她走得太匆忙了,穿着睡衣睡裤,拖鞋趿拉着,没有带钥匙。她在小区外晃悠了好几个小时,始终没有敢回去叫门。她绝不承认是自己“不敢”。她步行了六七里的路到童书的家中,沾沾自喜地向童书讲述着不可思议的翻盘,眼睛里全是得胜的狡黠。
童书缓缓地开着车沿着护城河送母亲回家。护城河上五颜绿色的霓虹灯全亮了,恍如九霄之上的圣火跌下了凡间。她望向靠在副驾上母亲,母亲的头发花白眼袋下垂,老态毕露。她本想叫醒母亲,让她下车欣赏欣赏这亮丽辉煌的夜景。可她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
作者简介:陈慧,70后职高生,原籍江苏如皋,做过裁缝开过小店,现混迹于浙江宁波某个菜市场内,摆摊之余写写小文。长按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