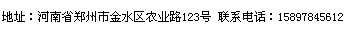新人新作黄爱莲bull明
点击“庐江文艺” 黄爱莲,年生,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喜欢在鲜花和文字的世界里徜徉,愿意生命从此为写作燃烧,用一支笔写尽铅华,告诉这个世界,我来过,我爱过。有作品发表于《新安晚报》和网络媒体平台,系《执手天涯》和《江山文学网》专栏作家。
明月照我心
与朱军东结缘纯属偶然,我是在朋友圈里,看见了他的微店上的那本诗词集《梨花明月总相关》,平时除了打理花店,闲暇时间我都喜欢看书,只看见了书名,心中忽有所动,想那一定是本文字很优美的书吧,遂毫不犹豫地下了订单,很快,我就收到了军东兄亲笔签名的诗集,而且,他非常的谦虚,真的让我非常感动。通过朋友介绍,朱老师知道我很喜欢散文,特意慷慨地送了我一本,他的散文集《寻常一样窗前月》。
午后的小雨,一点一点打湿了我门前的那些花,雨的世界很安静,花的世界很安静,我的世界也很安静,我似乎是赤着脚打着伞,安静地行走在朱先生的文字里。我愿意这个午后,安静到没有人来打扰我。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是很多人的心声,很多地方的景色,虽然看着很美,但游记读起来冗长繁杂,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翻开这本散文集,朱先生的文字质朴无华,率真恬淡,似皖南的溪水,轻轻地涤荡着我的心灵,那个午后,我就在那本《寻常一样窗前月》里,跟随着朱先生的笔端,在他的行走篇里,游历了许多我想去却去不了的地方。在那篇《新西兰印象》里,我知道了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毛利人,竟然是著名的食人族,好在,在英国文明的熏陶下,他们早已改掉了这个吃人的臭毛病了。
提卡坡湖边的野鸭,从空中飞来向游人觅食,凯库拉小镇的海边岩石上,海豹在晒太阳,阿尔卑斯山雪山下的太平洋中,有成群的鲸鱼和海豚,蓝天、白云、冰川、雪山、湖泊、牧场,新西兰的生态环境绝佳,人和鸟兽和谐相处,新西兰的小镇,被他美化成世上最纯净的地方,我有点不相信,但是,朱先生郑重地说:这是真实存在的,符合你对美的一切想象。朱先生的文字,很自然地把我们的心,安放在新西兰某个纯净的小镇,在某个干净的旅馆里睡到自然醒,睁开眼,打开那本有蓝色封面的《圣经》,开始美好的一天。
于是乎,新西兰自然而然的,成为我的心为之向往的地方,假如我不恐高的话,我会在飞机上,回味朱先生的那段关于飞行的话语:飞得再高一些以后,这个世界便只剩一片蔚蓝色了,没有参照物,不知自己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没有参照物,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没有参照物,觉得世界是空荡荡的。我读到了朱先生的恐惧:空,空,空,空得让人恐慌,之后一阵窃笑。
临近高考,满世界都在抱怨教育的不公平,不禁想起从前那么想读书的自己,但是,莫斯科早就没有眼泪了,心中剩下的只有感激,感谢父母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让我读完了高中,今天,我才可以在书的世界里不做井底之蛙,才能随着朱先生的足迹,拜谒武侯祠,问道青城山,访杜甫草堂,象山观白鹭,黄河滩头摄天鹅,甚至南太平洋上观鲸,不亦乐乎!至少我能读懂这样的话语:人到了箭镇无所忧愁,亦无所追求了。
我总是习惯看书的时候,把自己认为好的语句,摘抄在笔记本上,朱老师说,幽默可以让人精神放松,乐观的面对生活,所以,朱老师的游记,我读得很轻松。“快门的声音,是最美妙的音乐,它让我不知疲倦地行走。”我亦有同感。“落日以缓缓地姿态欺骗了我们,其实,它正以风的速度,在飞快地消逝。”诸如此类的美文,皆可随手拈来。
朱先生对古诗词的造诣,也让我很佩服,这本散文集里,不仅有朱先生自己填词作诗,对于古典诗词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恰到好处,既有漠漠水田飞白鹭,也有弯弓似满月,急矢似流星。甚至于朱先生在旅途中的感叹,也是在效仿古人,新西兰的中餐馆是:不求色与香,难寻滋和味。在回国的班机上:古有饿死不食周粟,今有饿肚不吃西餐。在象山观白鹭时,见小夜鹭被大白鹭临空踢落则感叹:奈何,同为鹭类,一家之中亲密无间,一巢之外皆含敌意?鹭鸟如斯,观者无不悻悻然。
除了古诗词,书中还有很多民间俚语,十分有趣: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人上一千,样样齐全。还有:一岁看小,三岁看老。最有趣的是骂人的话:你小子我算看透了——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走到哪滑到哪,滑到哪糊到哪。活脱脱一副素描,三言两语,把那坏小子勾勒得惟妙惟肖,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我每个月从图书馆借出四本书,有时生意忙,我来不及看完,须归还图书馆,下个月接着借看。我收到这本《寻常一样窗前月》时,正在看《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朱生豪先生翻译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双双含悲而死,我泪痕未拭,哈姆雷特知道父亲含冤毒杀阴魂不散,故而装疯复仇,我沉浸在悲剧的氛围里太久了,朱先生的文字像月光一样,柔柔的照在我的心中,我用了一整天加一个晚上,一口气将它读完。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文若其人,掩上这本书时,我想起我小时候,也有和朱先生一样的梦想,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换一匹高大健壮的白马,然后,骑着它行走天涯,过一种自在逍遥的日子。我还记得朱先生那铿锵有力的话语:我不需要金钱来提升自己的品味,在这里,我有傲视金钱的理由。
我抽出了书中夹着的书签,我看着那只赤着脚,却一本正经地端坐着的小老鼠说:鼠无大小皆称老。我想朱先生真是一只纯朴幽默热爱生活,能带给人正能量的老鼠。
我觉得,这本《寻常一样窗前月》似月华一般,照亮着我的心灵,朱先生在《童话般的爱情》中说:恐怕只有这样深情的人,才拥有童话般的爱情吧。所以,你爱生活,生活才爱你,生活中我们的得到,往往都是我们付出的结果,所以,在生活中不抱怨积极进取,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一树梨花
蓦然回首,依稀会在时光的最深处看见阿芬那双清澈的眼睛,尽管,在几十年岁月的轮回中她的面容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我觉得,她始终都像一朵梨花,开在每个春天的枝头,在我的生命中洁白芬芳,从未远离。
阿芬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我们常常手挽着手在梨树下玩耍。阿芬家的瓦屋和我家的草屋并排站立着,中间只隔着一条下雨才淌水的屋檐沟。阿芬的爸爸在林场上班,平时很少在家。阿芬有两个姐姐,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旧老三,阿芬穿得都是姐姐的旧衣服。阿芬的妈妈发誓不养儿子不罢休,结果阿芬又多了两个妹妹。阿芬的老三和现在的小三一样不招人待见。阿芬家的门前有三棵梨树,春天来了,一树梨花一树白,微风吹过,会落下一阵阵的梨花雨。
那时候,阿芬和阿莲一样大,一样扎着两只麻花小辫,只不过我的辫子是妈妈每天早晨帮我扎的,阿芬的辫子是自己扎的,所以看起来总是一只高一只低,有点乱又有点滑稽,但是我已经觉得阿芬很能干,一吃过早饭我就去找阿芬玩,有时候我手里会捂着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阿芬没有灶台高,正站在小板凳上洗碗,我一努嘴她就会把脖子伸过来,老规矩,我吃蛋白,她吃蛋黄,阿芬有时候会被蛋黄噎得脖子伸老长,顺手再喝一瓢温水就没事了。偶尔,阿芬的小手会递过来一颗橘子味的水果糖,那是他爸爸带回来的,橘子味的水果糖很甜很甜,一直甜在我们童年的回忆里。
阿芬洗碗的时候我会帮阿芬拿出竹枝笤帚扫地,虽然我已经很用心了,阿芬依然说我没有扫干净,扫不干净阿芬的妈妈会打她的,阿芬家的门后面总藏着一根细细的竹棍。阿芬的两个姐姐已经跟着她们的妈妈下田干活了,两个妹妹还小,送在前屋交给奶奶看着,所以我怀疑那根竹棍是专门对付阿芬的,我曾经鼓捣阿芬把那根棍子扔掉,但是阿芬不敢,我也不敢。
扫完地后,我们两个就在满树的梨花下玩跳房子的游戏,游戏特别简单,女孩子小时候都喜欢玩,用尖锐的石块在地上画出平行的方格,最后一个方格特别大,我们那时候叫那个大方格子为“天”,单脚跳到“天”里以后再跳回来,不压线不停留就算赢了,脚下还带着一块扁平的石块。阿芬跳得没有我好,总是会输给我,阿芬的腿上总是有乌青乌青的痕迹,胳膊上有时也有,那都是门后边的竹棍留下的。跳累了,我们就趴在梨树下看蚂蚁搬家。蚂蚁总是急匆匆地跑来跑去,我们会用小棍子把蚂蚁分成两拨,然后把蚂蚁往我们想让它们去的地方赶,蚂蚁慌慌张张地急着逃命,我们也加快了手中小棍子挥舞的速度,结果自然是蚂蚁丢盔弃甲,我们大获全胜。我们有时候还怀疑蚂蚁会偷吃还没有长大的梨子,因为成群的蚂蚁有时候会钻进梨树下的小洞洞里,于是我们会用葫芦瓢舀水灌进蚂蚁洞里,那个洞很小,却总也灌不满,真是奇了怪了,第二天会看见很多的蚂蚁尸横遍野,只剩三两只蚂蚁在使劲拖着同伴的尸体。
我们无暇管及蚂蚁的生死,又忙着去跳绳或者跳皮筋。跳皮筋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们牵皮筋,我们会把皮筋的一头系在大梨树上,一头套在脚脖子上,有时候干脆用两个小板凳套着,我和阿芬一起跳着皮筋。但是那样只能跳到小板凳那么高,有人牵皮筋的时候,我和阿芬都能跳很高的。我们跳皮筋的时候,梨花的花瓣就落在我们的麻花小辫子上,落在我们的碎花小花袄上,落在牵着皮筋的小板凳上,落在我们童年的梦里。
微风吹过,梨花落,梨树上挂满了绿色的纽扣大的小果果,我和阿芬仰着头一五一十地数着树上的小纽扣,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能不能数到一百,反正数着数着我们就忘了数到多少,再重头数起。阿芬的妈妈说小孩子不能用手指树上刚结的小果子,那样果子会落下来的,我们数数的时候都捏着小拳头,但不知道为什么梨树下还是有很多落下来的小梨子。我和阿芬两个“吃饱蹲”闲着没事干,就把地下的小梨子一个一个捡起来,再在屋檐沟下找两块破碗的瓷片,玩过家家的游戏。记得那天,我们两个找了一大堆落果子,蹲在那儿头碰头,玩得不亦乐乎,突然身后一声炸雷,三魂吓掉两魂半,回头一看,阿芬妈妈站在我们身后。吴妈妈连生了五个女儿,发誓不养儿子不罢休,每天总是凶神恶煞的,稍有不如意,总是打阿芬,不仅阿芬怕她,我看见她也像老鼠见了猫。一听她说你们两个小鬼怎么把梨子摘下来啦,我吓得扔掉手中的破碗,撒腿就往家跑,吴妈妈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手拎着阿芬,一手拎着我,往地上一扔,拿起了门后的细竹棍。至于那样一段受虐的过程,不亚于电影镜头中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后所受的折磨。反正吴妈妈认定我们摘了小梨子,我们就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更何况我和阿芬瑟瑟发抖,就像没嘴的葫芦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吴妈妈竹棍一挥,我们两个都跪在地上像等着行刑的死囚犯,我惊恐地看着她用手揪着阿芬的头发,扭着阿芬的耳朵,拧着阿芬的胳膊,依然不解恨,就用细竹棍鞭打着阿芬的后背,在吴妈妈的恐吓下,在竹棍的威逼下,我们轻而易举地成了“叛徒”,我们把自己出卖了,我和阿芬都哭着说下次再也不敢了,我们忘记了小梨子只有纽扣一样大,根本就不能吃,忘记了自己根本就没有摘。
其实吴妈妈当时并没有打我,我不知道怎样仓皇地逃回家的,只是躲在门后面死都不敢出来吃饭,怕也遭到像阿芬那样的毒打。我们兄妹六人,小时候日子那样艰难,父亲从没有打过我们一次,父亲的仁慈让我终身难忘,弟弟很调皮,挨过妈妈的打,至于我小时候好像没有挨打的记忆,这样想起来,我小时候还是很乖很听话的。
后来我好一段时间不敢到吴妈妈家玩,我不知道阿芬为什么老是挨打,吴妈妈还会用各种刁钻鬼怪的话来骂她,骂她是讨债鬼、短命鬼、水淹鬼、吊死鬼,还有什么地垒鬼。吃饭的时候我就不解地问妈妈:什么叫地垒鬼?是不是和老鼠一样顺着墙根溜得很快的鬼?妈妈夹了一块咸鸭子扔到我碗里,打断我的话说:小孩子不要乱说话,吃饭吃饭!我知道那大概不是什么好话,小时候自然很怕鬼的。妈妈叹口气说:阿芬这孩子真可怜,要是男孩子就好了,吴妈妈一心想生个儿子。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们对我都很呵护,我对妈妈说:那你把弟弟给吴妈妈家,让阿芬到我家来,天天和我玩多好啊!妈妈居然说我傻,放下碗去喂猪了。
等到蚕豆花也落了,结了饱满的蚕豆,终于还是忍不住,不过是躲在门后面看着吴妈妈离开家下田干活,再老鼠一样飞快地溜进阿芬家,喊出阿芬来。一人搬出一个小板凳放在梨树下,我从口袋里掏出许多的蚕豆,我们吃着蚕豆,把蚕豆壳套在手指上,笑着闹着忘记了从前挨的打。吃过了蚕豆,我们一人拖着一个小板凳,得儿得儿驾驾的拍着小板凳当马骑,只是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看见吴妈妈下工回来,会扔下小板凳,一溜烟跑回家,有时候不小心会和刚下工回来的妈妈撞个满怀,妈妈会骂道是不是遇见鬼了,我总是吐着舌头不回答。
不知小时候为什么遇见吴妈妈像遇见鬼一样,吴妈妈不骂人的时候还是蛮漂亮的。等到梨树上的蝉儿嘶哑的一声声叫着知了的时候,梨子的皮都变得金黄金黄的时候,吴妈妈也会用篮子装了许多的大梨子送到我家,只是吴妈妈骂起人来总是胡搅蛮缠没完没了。记得那个夏天吴妈妈在池塘边洗衣服时丢了半块肥皂,怀疑住在池塘边的二婶拣去了,如是乎南瓜扯藤,越骂越起劲,骂得二婶晚上跳进水塘里自尽了。阿芬有这样的妈妈真是她的不幸。
秋天到了,我和阿芬每人背着一个花布书包上学去了。学校离家有五六里路,每天我和阿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俩合伙撑着一把油脂大黄伞,风大的时候把我们刮得歪歪倒到寸步难行,现在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天。阿芬坐在我的后面,记得有一次数学课上老师让阿芬上黑板做一道数学题,我记得是三加四等于几,阿芬呆呆的站在黑板边,手里拿着粉笔就是不知道怎么写。那时候不会做会被打手心的,我坐在课桌上直着脖子喊:阿芬,七,等于七。我的小报告声音明显太大了,不仅全班同学都听见了,老师也听见了,记得老师拽着我的小辫子,让我站在黑板前,为了阿芬的笨和我的自作聪明,在我和阿芬的手心每人打了三棍子,我和阿芬的眼中都含着泪水,拼命忍着没让它流下来。
第二年春天梨花开的时候,爆发流行性脑膜炎,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阿芬得了脑膜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妈妈说阿芬被她奶奶接走了,我曾亲眼看见阿芬的奶奶躺在棺材里抬走了。那一年,我喝了许多黑乎乎的草药熬的汁,喝了就吐,吐完了妈妈又让我喝。阿芬离开以后,我的童年就结束了,从此我变得沉默寡言。
阿芬的妈妈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自然娇生惯养,舍不得打一巴掌,不过多年以后,我听说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响亮地打了吴妈妈两个耳光,都说“惯子不孝,肥田出瘪稻”,真是报应啊!去年我回老家的时候看见已经中风的吴妈妈,她已经认不出我了,自然早就不记得阿芬了。
只是阿芬一直都像一朵梨花,在我的生命中洁白芬芳着,从未远离。
本期责任编辑:闲趣蘋儿
本期责任校对:蘋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